“在中国喝醉”:李杜的诗酒与英译
作者:孙红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美国人桑德豪斯(Derek Sandhaus)的《在中国喝醉:白酒与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Drunk in China: Baijiu and the World's Oldest Drinking Culture)(2019年)是一本类似于中国酒文化大观的书,谈论酒在中国的历史、酒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在书中李白、杜甫等好饮的诗人一一登场,共同展现了诗酒的斑斓多姿,彰显了醇厚的中华文化。在桑德豪斯看来,酒之于中国,犹如“文明之血液”。这是一个有着七千年饮酒历史的国度。当一个人饮一杯中国酒时,“便融入了一个七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

陈洪绶《李白宴桃李园图》(1650) 资料图片
一、杜诗与“浊醪”
《在中国喝醉:白酒与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的卷首引用了杜甫《落日》一诗的尾联“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作为题献,英译为:“噢,酒,谁给了你微妙的神力?/只需一小杯便可以淹溺千种的愁。”作为一部介绍中国酒文化的书,这是一个极为巧妙的选择,一开始便将诗与酒、酒与人生联系在一起,表述了酒对于中国人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性。它的英译并非出自桑德豪斯之手,而是引自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120多年前所译的一个集子《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s)(1898年)。在原来的译本中,翟理斯将《落日》的题名换成了《酒》,但在这里,桑德豪斯又重新改为原名。翟理斯的译笔浅白晓畅,不过 “浊醪”与“散千愁”两处均未译出:前者指未经过滤、粗制的酒,后者指史册所载的一种被东方朔命名为“怪哉”的小虫,遇酒即化,故有“散愁”之说。
“浊醪”一词自带粗粝之感,有随性之意,不讲究精致。老杜尤其喜欢拿这个词来指称酒,在诗中屡屡使用:“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浊醪自初熟,东城多鼓鼙。”“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等等。这一方面和他潦倒的生活状态不无关系——他常常囊中羞涩,无沽酒之钱:“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大诗人胸怀旷达,能够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另一方面也有审美的考虑:“浊醪”的要义在于不修边幅,在于一种质朴无华的感受。“葡萄美酒夜光杯”反而太过强调那种雕琢、修饰、工整的意味,不若“浊醪”来得天然纯粹,这正是“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的道理:纵是浊酒,几杯下肚,亦可让人陶然忘忧,暂不必挂心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浊醪”这个小小的词,宛若不经意间在文字中投下的石子,激起细微的波澜,制造了意义表达的起伏荡漾。若无它在场,诗歌则如一潭止水,太过平淡无奇。由此可见,从文化中提炼出的掌故,既可为诗文增色,亦可以含蓄地表达内容和思想。这么一来,诗的一呼一吸,都牵连着文化的脉搏。可惜这一层多余的意蕴在译文中完全消失了。
此外,浊醪、醪糟等词也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所理解的“wine”的酒文化,其中牵涉中国的传统酿造工艺。
济慈《夜莺颂》里这样写道:“啊,但愿饮一口美酒,/一口曾在地窖冷藏多年的佳酿!”诗中,“美酒”用的是“vintage”一词的本意。无论是“wine”还是“vintage”,共有的词根均是“vinum”(葡萄酒),与vineyard(葡萄园)等词均指向了葡萄这一原材料。古罗马人说:In vino veritas(酒中有真理或酒后吐真言),vino便是葡萄酒。与之相比,醪糟、浊醪等词指向的是谷物类酒,从原材料到酿制工艺都大不相同。以“wine”译“浊醪”,这种方法对于译者而言自然简单易行,不过也暴露了酒在跨文化的旅行中所遭遇的屏障。在很多情况下,译文很难还原其原初语境进而曲尽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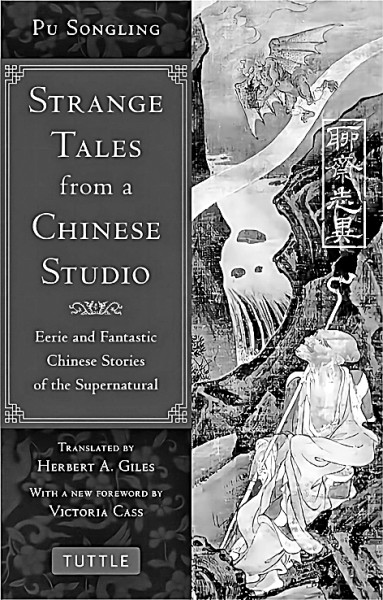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 资料图片
二、谷物酒与葡萄酒
关于“酒”字翻译的难度,一百多年前,翟理斯在较早介绍中国酒文化时便深有感受。他认为:现代中国的酒和孔子时代的酒并无二异,都是“由米发酵、蒸馏的烈酒”,“虽然大量诗文显示中国人在历史上也饮用葡萄酒,但这种酒自15世纪后便消失了”——当然,他的判断并不准确,酒的蒸馏技术一般认为开始于元代,中国的酿酒在原材料、工艺等方面也要远比这句话所传达的信息复杂得多。不过,翟理斯主要是为了强调中国的“wine”并非西方人普遍理解的“葡萄酒”,以及用“wine”来表达中国酒只是权宜之计,这么说也无可厚非。虽然在谈中国的酒文化时,他援引了古雅典的饮酒风俗来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文化之间有着诸多共通之处,都热衷于饮酒时划拳、赋诗、听音乐,都喜欢在饮到酣畅处换上大杯,“在中国的小说中,半醉的英雄人物总是毫不例外地叫嚷换上大的杯盏”,但是,看似有可比之处的两种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桑德豪斯的著作也提及了“酒”与“wine”对译的问题,强调“‘酒’在中文中是一个表意极为宽泛的词,用来指称所有含酒精的饮品,包括白酒、黄酒、啤酒和葡萄酒,使得它的翻译在多数情况下困难重重”。再者,白酒之中,又有不同的品类,如各种香型的区分也不可混为一谈:“就像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的分类一样,它们除了有着共同的起源,其他方面几无可通约之处。”桑德豪斯对中国人的造酒术进行了考古,指出“曲”的发明至关重要,让中国酒的历史演化从此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重要性不啻于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实际上,他没有提及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中,“曲”会被用来指代酒。元代白朴《寄生草·饮》中写道:“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从酒糟到浊酒(也即“醅”),再到“酒曲”,恰巧涉及了中国酒的酿造技术。
不过,唐代的酒既有谷物酒,也有葡萄酒,既有“浊醪”,也有玉液琼浆。如翟理斯所言,至少在一段历史时期,谷物酒与葡萄酒都是存在于中国的饮品,只是后者更加珍贵稀有。美国著名学者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在《撒马尔罕的金桃》里谈及唐朝的“外来物”时,就以酒为例,聚焦了中西文化交往之中的葡萄酒。其中《葡萄与葡萄酒》一节写道,中国人早就“精通从谷物中提取发酵性饮料的方式了”,到了唐朝,“稻米已经成为酒精饮料的主要来源”。不过,随着唐王朝的日益发达,外国佳酿也传入中土。“唐朝统治初年,由于唐朝势力迅速扩张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内变得家喻户晓”,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也随之传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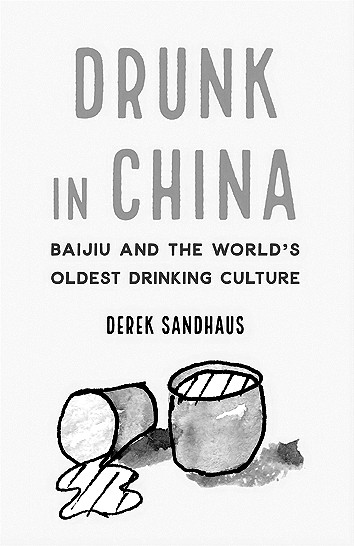
《在中国喝醉:白酒与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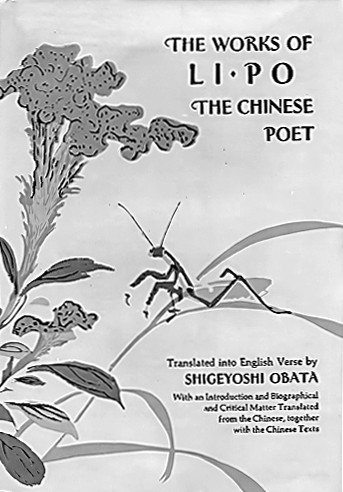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 资料图片
三、“糟丘”的译法
李白诗中,谷物酒和葡萄酒可以并举。《襄阳歌》里有一句:“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在这里,谷物酿的酒(曲、糟)与葡萄酿的酒共同存在。“糟丘”一词如其名所示,涉及中国粮食酒的发酵、酿制方式,指的是酿酒后堆积如丘的酒糟,从而被用来指代大量的酒。不过,就译诗而言,“糟丘”应是一处难以处理的文字。译者要么加以简化,不附任何说明,如《聊斋志异·酒友》有“糟丘之良友”之说,翟理斯译作“酒友”,以英文习语对译中文习语,既地道又精准,相较于拖泥带水的加注式翻译反倒浅近又富有生趣,是极成功的译例。“糟丘”这个词多次出现在李白诗中——“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李白好酒,并且海量,而“糟丘”所指为“酿酒之多,沉湎之甚”,这个词当然颇得他的欢心。如果“浊醪”是杜甫的心头好,那么“糟丘”或许是李白的最爱。闻一多先生谈日本学者小畑薰良的英译《李白诗集》,曾批评他没有进行适当的甄别,疑似伪诗收了不少,却没有收录《襄阳歌》等佳作,令人遗憾。小畑薰良译本收录了《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译文也是删繁就简,取了捷径,未译出“糟丘”一词。
在闻先生看来,小畑薰良的译本不乏疏漏之处,比如“风流”译作“wind and stream”,“燕山雪大花如席”的“席”译作“pillow”,“青春”译作“Green Spring”。
不过,小畑薰良的译本,也有可击节叫好之处。如《金陵酒肆留别》一诗的翻译,“吴姬压酒唤客尝”译作:“While the pretty girls of Wu bid us taste the new wine”(吴地美丽的少女请我们品尝新酒)。译文读来生动活泼,尤其是“新酒”一词既浅切形象,又天真烂漫。原诗中的“压酒”是汲取新酿的酒,“米酒新熟,压而取之。”小畑薰良将这个细节去掉,直接译作“新酒”,应属“就地取材”。一来西谚有源出《新约》的“旧瓶装新酒”一说,引入此处信手拈来又合乎情理;再者,“新”一词也可能不小心泄露了这部译诗的一个参照对象:小畑薰良自序中提及大诗人庞德由日文转译的李白诗歌。20世纪初,为了一反英美诗坛陈陈相因的现状,庞德将中国古诗作为改观英语诗歌的源头活水,提出了现代派文学的著名口号“make it new”(日日新),它便源自《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新”字概括了现代派诗学主张的内核,影响深远。当代汉学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先生所编中国古诗集《中国古典诗歌新选》(The 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采撷了李白、杜甫等历代诗人的名作,封面上便写着几个大大的汉字“新日日新”,也是与20世纪初的“尚新”之意形成回响。
显然,小畑薰良此句的翻译对原诗的信息进行了取舍,可谓旧瓶装新酒。这一改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闻先生也指出:“但是翻译当然不是给原著的作者看的,也不是为懂原著的人看的,翻译毕竟是翻译,同原著当然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件译品要在懂原著的人面前讨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酒文化的传译自然也不必非要拘泥于字面意义上的完全对等,有时需要采用适当的归化手段,将酒译成熟识的酒;有时则需要异化的传译,作为一个陌生物、舶来品安放到另一个语境中,引发不同的想象。

翟理斯 资料图片

德加《苦艾酒》(1875-1876) 资料图片
四、“舶来品”与共享的诗意
唐朝人热衷于将新奇的事物入诗,变成一种特殊的意象。“葡萄酒在当时的确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薛爱华指出,“在8世纪时,葡萄虽然已经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然而杜甫还是在一组新奇陌生、非汉地物品的比喻中使用了葡萄这个词。他在诗中以‘葡萄熟’对‘苜蓿多’——两种植物都是在公元前2世纪时由张骞引进的,而且都是相当古老的比兴对象,在这首诗中,杜甫还以‘羌女’与‘胡儿’相对。”在李白的诗中,葡萄酒、金叵罗、鹦鹉杯,都属于相对陌生、稀有的事物,因而天然带有几分神秘和浪漫。薛爱华说:“舶来品对人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一个陌生文化的名字总带有一丝神秘感。即使我们对于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明就里,也不认识以此为称呼的人,也会觉得它带着某种异域的、审美的色彩。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第一句就是忽必烈汗在大都建了座长乐宫。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大都”,诗人都是要一下子就把西方的读者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钱钟书先生就说过,不识地名人名之美者不足以言诗——如果从地名、人名里体会不到美,就缺少一种谈诗的感性了。
在一定程度上,名物的稀有性,也赋予其一种特殊的陌生感,或者是音乐感,然后让我们觉得它所形容的人或者物是超凡脱俗的。从文化交往的另一端看李白,道理也是相通的。无论是他的好饮,还是他的诗名,皆是陌生的存在,所以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天然地具有诗意或者是浪漫感。当代爱尔兰诗人马洪(Derek Mahon)有一首题为《一个好奇鬼》的诗,其中写到了曾任船长的岳父,并设想了在另一种生活里和他转换了身份,这位船长可能是一位诗人,而自己则是一名水手:“……我曾申请加入商船海军/却未通过视力测验/后来沦为一个疯癫的抒情诗人。/你如李白一般失衡落水后,/他们在你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未发表的诗篇。”这里将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和自己的岳父相提并论,将诗的艺术追踪到遥远的异域与久远的年代,通过这种跨越表达了诗的亲切、朴素与恒长。诗并不专属于某个群体,而是一种跨越民族、超离时空的共有的艺术。
太白好酒,有“因醉入水中提月而死”的说法,虽是传说,不过却也符合他的气质,对此西方人亦有耳闻。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对此就有提及。桑德豪斯所编写的中国酒的编年史专门列出了李白的出生年份,第二章篇首便援引了李白的《将进酒》,也提及了他醉酒后在扬子江中捞月溺亡的传说。在另外一首诗中,马洪写到了“黄河月色”,让人想到了李白诗中的黄河意象。中国的黄河与爱尔兰本土的景观毫无违和感地出现在同一首诗中,形成了一种新奇的回响。无论李白用“葡萄酒”“金叵罗”,还是马洪用“李白”“黄河月色”,两个相对陌生的名词,将这两首诗预设的读者瞬间迁移到另一个时空之中,传达了神秘的诗意。
酒可以引起颇具浪漫色彩的想象,成为一种文化、一个人群、一个时代的文化表征物。酒也因为这样的联系具有了个性——朗姆酒让人想到了海盗,杜松子酒让人想到18世纪的英国民众,想到荷加斯的画,苦艾酒让人想到19世纪的欧洲艺术家,想到凡·高、波德莱尔。酒自然也能成为某一人物最具标志性的符号,比如詹姆斯·邦德总要饮一杯:“马提尼,摇晃,不要搅拌。”真实的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大诗人布罗斯基来到美国,留给当时英美诗坛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嗜饮绝对牌伏特加,以至后来的倾慕者也要买来品一品滋味儿;又如,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侄女写的《美国大作家的烹饪书》详述了福克纳“秘制”的热托蒂酒——一种据说可以治疗感冒的甜酒的制作方法,让这种酒从此沾上了福克纳的记忆。
在世界文化中,李白、杜甫素有酒名,酒也成了他们的一种标志性符号。从翟理斯,到小畑薰良,再到桑德豪斯,他们所收录的李白、杜甫的诗歌中,饮酒诗占十之六七,连题目中都处处点缀了酒的字眼,当然也播散了他们的好饮之名。在酒与诗的故事里,折射了人性各种复杂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古今、中外均可以共情、互通,我们在人生得意时,会开怀畅饮:“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在失意后,也会举杯痛饮、慷慨悲歌:“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这些诗歌让诗人不朽,也让我们在推杯换盏或对影独酌时“融入一个七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