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她曾生活在梦幻大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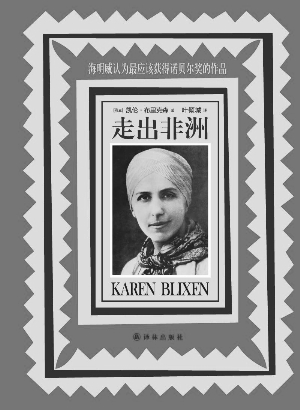
《走出非洲》
[丹麦]凯伦·布里克森 著
叶倾城 译
译林出版社 2014年6月
这部自传小说,描绘了作者1914年至1931年间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生活故事,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1986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作者以优美、缓慢而又忧伤的散文式语言讲述了她一生中最丰富和最美丽的回忆,在非洲那片土地上她倾注了太多的感情,而对于最终远离非洲的悲伤,她久久未能平复。
云端的非洲
我从前在非洲有个农场,就在恩贡山脚下。农场海拔一千八百米,在它北向一百六十公里处,赤道横穿高原。白日里,你会觉得身在极高处,太阳触手可及。拂晓与薄暮却闲适清澈。夜间很冷。
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海拔,共同绘制出一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画卷。那里并不肥沃,也不华丽;这是被海拔一千八百米净化过的非洲,是这片大地朴质且微妙的精华所在。色调总是干枯灼黑,像烈火烧制过的陶器上的釉彩。树叶都轻盈细致,树木的构造也不像欧洲树木,会生成拱门状或圆顶形,而是矮矮地贴着地面。那些孤零零矗立着的参天大树,像棕榈树,或者满载的船,风帆早已卷起,周身笼罩着史诗般的浪漫气息。树林的尽头形状飘忽不定,仿佛全世界都在轻轻摇晃。一望无尽的草原上,丛生着歪歪倒倒的荆棘树,全是老树枯藤,光秃秃的。草叶闻起来像百里香和沼泽桃金娘,有些地方,气味馥郁得几乎冲鼻子。无论平原上的万千花朵,抑或原始森林里的藤蔓和攀缘植物,都和低地植物一般小巧——只在漫长雨季开始的时候,大朵的、芬芳四溢的百合花会瞬间绽放。一望无际,一切你眼中所见,都生而庄严自由,有着难以想象的尊贵意味。
一旦生活于此,你感受最深的,一定是这里的空气。每一次回首非洲高原的旅居岁月,那种似乎生活在云端的感觉,会深深震撼你。天色是淡薄的湖蓝或紫,云朵澎湃,既厚重又轻若无物,云头高高扬起,仿佛即将扬帆远走。天色的蔚蓝里,蕴藏着勃勃的生机力量,为不远处的群山树林染上一抹新鲜的明蓝。正午时分,地面上的空气躁动起来,仿佛燃烧的焰影;它闪烁着,摇曳着,流光如大河奔腾,它映照一切,使万事万物都形影相对,缔造出壮观的海市蜃楼、仙世魔境。
在高海拔的空气下,你呼吸顺畅,脏腑间既轻盈又踌躇满志。每一个高原上的黎明既起,你都会想:我来了,来到了属于我的地方。
收割咖啡果
咖啡园里有几幅图景美不胜收。雨季初来,盛放的花朵闪着微光,在迷雾及蒙蒙细雨中,宛如粉笔绘出的云朵,笼罩在二百四十公顷咖啡园的上方。咖啡花有一种淡淡的、略带苦涩的芬芳,像黑刺李花。当大地被成熟的咖啡果染红,所有的妇女和所有的孩子——当地人称为“图图”的——都倾巢出动,和男人们一道收割咖啡果。随后,大大小小的牛车,全部整装待发,把咖啡豆运送到河边的工厂。我们的机器状态向来不稳定,从来没法确定会发生什么,但这工厂是我们自行设计筹建的,难免敝帚自珍。巨大的咖啡烘干机转呀转呀,在它的铁胃里,咖啡豆互相摩擦,声音像海浪正在冲刷海岸。有几次,咖啡烘干准备出炉的时分正是子夜前后。那真是惊艳的一刻,高大幽暗的厂房里,挂满防风灯,处处结着蜘蛛网,遍地咖啡豆的外皮。在灯光下,一张张闪耀着兴奋的黑色脸孔,围在烘干机周围;你会感觉到,整座工厂,在这不寻常的非洲之夜,宛如阿比西尼亚人耳垂上一颗璀璨的宝石。随后,咖啡豆被脱壳、分级、手工分拣,装入麻袋打包完毕后,用缝马鞍用的粗针大线将麻袋封口。
黎明将至,夜色还昏蒙,我躺在床上,听见大车的声音。十二袋咖啡竟重一吨,十六头牛拉一辆车,每辆车上,装满咖啡的麻袋垒得高高的。它们上路了,去往位于远方工矿山区的内罗毕火车站。一片叫喊吵嚷的声音,车夫们跟在牛车两侧跑。我很高兴这一条路基本都是下坡,只有一处上坡,因为农场比内罗毕城地势高三百米。傍晚前后,我走出门来迎接返程的队伍,空空的大车前方,牛累得低垂着头,一个疲惫不堪的小孩领着它们;倦透了的车夫,手里的鞭子无力地拖曳在道路上的扬尘间。现在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了。咖啡一两天后就要扬帆出海,我们只能祈祷在伦敦拍卖市场上能交个好运气。
结交原住民
与原住民结交并不容易。他们听力敏锐,天性敏感,一旦被吓着,便在一秒钟之内缩回自己的小世界,正如野生动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你身边消失——转眼间逃之夭夭。
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明确答复,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已经和他们混得很熟。直截了当的问题,比如他有多少头牛,他总应对得躲躲闪闪:“跟我昨天告诉你的一样多。”这样的答法,很伤欧洲人的感情;就像这样的问法,伤了原住民的感情一样。如果我们对他们施压,或者穷追不舍,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一个解释,他们就尽可能地回避敷衍。一旦我们干扰到原住民的存在,他们的表现就像蚂蚁一样——当有人把棍棒捅进蚁冢丘,蚂蚁大军会发挥出难以想象的顽强和坚毅,无声无息地,迅速清除被损毁的部分。
我永远不会真正懂得他们,理解他们,他们却把我看得透透的。我还在犹豫不决,不曾下定决心,他们早已知道我最终的决定。一度,我在吉尔—吉尔有个小农场,在那里住的是帐篷。我经常在恩贡和吉尔—吉尔之间乘火车来回。我在吉尔—吉尔的时候,一旦下雨,就得仓促回家。返程站是吉库尤站,离农场还有十六公里,我下车时,总发现一个仆人已经等在那儿,还带着一头骡子供我骑乘。当我问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回家了,他们会看向远方,表情很不自在,像被吓着了又像觉得无聊。假设一个聋人坚持要我们给他解释何谓旋律,估计我们也是一样满脸尴尬。
当原住民渐渐习惯了突如其来的喧哗和行动,萌生安全感之后,他们会对我们说很多,坦率程度远胜欧洲人之间。他们不可信赖,但十分真诚。一个好名声——或称威望,对原住民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大体而言,农场生活非常孤独,夜晚静滞,只听见钟摆的滴滴答答,仿佛你的生命也随之一点一滴流逝,而每时每刻,我都能意识到原住民生命中那令一切黯然失色的静默,与我自己的静默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两种沉寂,彼此呼应。
原住民就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非洲。
在非洲的野外狩猎
远征狩猎期间,我见过一群野牛,共有一百二十九头。在铜红色的天穹下,自黎明的薄雾间,一头接一头走出来,像一群黝黑、魁梧、钢铁铸就的巨兽,硕大的角在它们头上水平摇动着,它们好像不是一步步走近我,而是在我眼前被刹那间练就,一完工就落地成型。
我也见过一群大象,穿行在密密的原始森林,阳光从藤蔓的缝隙间点点滴滴射下来。大象们从容迈步,仿佛与世界尽头有个约会。世界尽头一定漫无边际,如同一幅非常古老、极其珍贵的波斯地毯的边缘,绿、黄、黑棕色彼此交织。我也曾一次又一次,屏息注视着长颈鹿们成群结队穿过草原,它们的趣致、独特及植物一般的沉静,让人恍然不觉是一群动物,而仿佛是一种罕见的花卉,抽着长长的花柄,花瓣硕大无朋,还洒满斑点,这花之家族正缓缓向前。
清晨,有两头犀牛在闲荡,而我悄悄跟在它们身后,看它们在黎明的冷空气里,又打喷嚏又擤鼻子——如此寒意逼人,鼻子觉得不舒服吧?看上去,它们像两块在山谷间滚动的巨石,棱角分明,且自得其乐。
还有一次,我邂逅了一头雄狮,正是日出之前,残月当空,它刚完成杀戮,穿过灰色旷野回家去,暗黑的身影投在闪着银辉的草尖上,被血染红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也有一次,我遇到的狮子正在狮子家族的前呼后拥下,心满意足地午后小憩。在这片非洲狮的乐园里,金合欢树展开宽宽的枝叶,狮子就睡在它泉水般清凉柔和的树荫下。
不管农场生涯多么沉闷,回想起这所有,都让人欢欣雀跃。大型动物都还在那儿呢,在属于它们自己的世界里;只要我想,随时可以去探访它们。它们近在咫尺,像生活中的一道光,给农场带来了鲜活热闹。法拉赫以及曾随我打过猎的原住民佣人们,都日夜盼望着远征狩猎。
在野外,我学会了绝对不要突然有动作。跟你打交道的这些生物,是害羞且警觉的,天生就想避开人类,虽然你非常不希望它们如此。开化了的人类已经失去静默的本能,必须学会安静,才能被荒原接纳。猎人,尤其是手持照相机的那一种,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缓慢移动的艺术,绝不能轻举妄动。猎人不可以自行其是,必须顺依荒原的规则,包括风、颜色以及味道,彼此步调也得保持一致。有时猎物反反复复,做同一个动作,猎人也得蹑足跟踪于其后。
一旦掌握了非洲的节奏,你会发现,它们也深藏在非洲音乐里。野外狩猎的经验,当我与原住民打交道的时候,也派上了用场。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