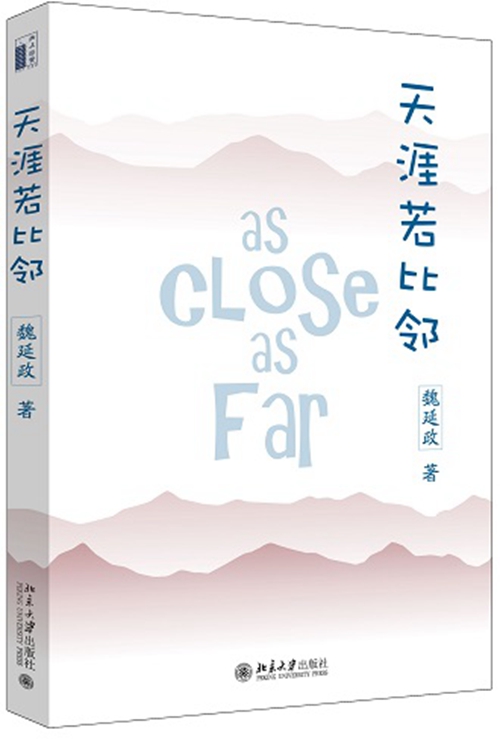
(本文摘自《天涯若比邻》,魏延政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作者简介:魏延政,北大校友,2011年不幸确诊罹患世界罕见癌症,2012年右大腿截肢后离开工作岗位。在抗癌期间,坚持不懈地读书撰文,在大型企业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分享传播东西方文化、欧美高端市场拓展、系统化思维、大型企业流程管理、产品管理以及人生幸福理念。2015年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面向全球各企业中高层主管开设的复旦哲学大会课堂上,多次主讲《读书吧,虽然这些知识终将随着我们的生命而去》《系统化思维——人生幸福最大化》《当霍金说“哲学已死”时,他在说什么?》《哲学的一万种可能》,获得众多文化、哲学爱好者的好评。不幸的是,2016年年初癌症扩散。在病重垂危的时刻,为指导儿子未来的成长,撰文《人生若如几回忆》,感动了众多“魏延政智库”的读者。
人生若如几回忆
朋友,你可曾想过,假如某一刻你的生命倏忽而去,你该给你最挚爱的人留下些什么?几年前化疗的时候我想过这个问题,后来又活过来几年,这个思考又被抛诸脑后。这段时间病魔肆虐,我犹如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躺了半年动弹不得,这个问题便又盘绕在脑海中。人的一生究竟活了些什么?大多数人都懒得去考虑这样的问题,或者想不清楚,等到真能想明白点什么的时候,往往是隐退江湖多年,或者是病到离死不远的时候。
前些年,在我癌症截肢后最无助的时候,某500强企业向我踹了最狠的一脚——终止合同,人生惨淡莫过于此。我骤然变得如同一片鸿毛一般,无着无落地飘荡在半空中,当时我设想了一下人生百年可能会有怎样的百态,细想一下也不过如此:人生啊,活到一十,横着竖着都一样;活到二十,睡着醒着都一样;活到三十,公司家庭都一样;活到四十,博士文盲都一样;活到五十,当官百姓都一样;活到六十,有钱没钱都一样;活到七十,睁眼闭眼都一样;活到八十,男人女人都一样;活到九十,有腿没腿都一样;活到一百,死了活着都一样!
人能活到像《圣经·创世纪》里那些人那样动辄千岁吗?若真能,人最终能记得自己这一生究竟是谁、做过些什么吗?第一个一百年做中学教师,当老师当厌倦了,第二个一百年做珠宝生意……如此下去,活着怕是一种负担,未必每个人都想活那么长。所以人生百年最好,不胜其烦,在丰满到装不下的时候落幕,恰到好处,一生所爱仍历历在目。
人一生能爱过几次?第一次的爱,是依恋,孩童对父母的爱,是用一生来回味的;第二次的爱,是寻觅,我们总是抱以最真诚的愿望,却往往未成眷属,是用后半生来忘却的;第三次的爱,是相伴,人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一阶段如画卷一点点展开,我们沉浸其中,来不及欣赏每一段的美好,只得须臾回想起彼此初见,岁月流年,她可能有某些不如意,但她永远定格在那个最风华动人的一刻,只有她是用一生来相守的;第四次的爱,是回报,一个小生命的降临,抱在怀里满心欢喜,一时不见满是挂念,是用一生的感悟来回报的。
我算是幸运的,四次爱都经历过。一生所爱情真意切的几个瞬间,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三岁的时候发烧,一个清凉的夜晚,妈妈把一片阿司匹林切成四瓣,给我喂了一瓣,然后到院子里给我把尿,我看见月亮很大、很圆、很亮;五岁的时候,爸爸带我爬红山,我跑得比他快,下山后看见羊肉串,爸爸给我买了二十串;七岁的时候,二姐放学后把我抱在腿上讲她英语课本中渔夫的故事,大姐在做饭,那时常常停电,炉火把大姐的脸映得通红;九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把所有楼门的螺帽偷回家,我心里非常不安,下午又偷偷把螺帽一个个全部装回去,比上午偷螺帽时更紧张;十二岁的时候,晚上做不完数学竞赛题,妈妈说“不着急,妈陪着你,做不完,你不睡觉,妈也不睡”,父亲串门回来,也坐在一旁陪着我,有不会的难题,父亲就来帮我。父母已老,我限于行动不便,愿有一日能回到故土给二老正正经经磕个头,感念养育之恩。我是不是老了?越久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人一生究竟能有几个瞬间让你挂怀?
中间的几十年,就像过场,横着竖着、梦着醒着都一样,忙忙碌碌含辛茹苦几十年如七日:忙day(Monday)、求死day(Tuesday)、未死day(Wednesday)、索死day(Thursday)、福来day(Friday)、洒脱day(Saturday)、伤day(Sunday)。全球语言虽有不同,意义却毫无二致,终究从忙到伤,又带着伤回到忙。有时我从现年75岁的父亲那里也能学到不少哲理,他说人到70岁自然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便是孔子说的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吧,父亲读书不多,人生经历和哲学都来自实践。
终于有一日,生活有了不同。35岁的时候,我牵着她的手漫步苏堤,一起唱着《恋曲1990》,那个时节,裙正飘摇唇正红;翌年,她坐在大皮球上,我拖着她的胳膊,以便小生命向下运动降临,医生初时还问我,过会儿会出很多血、会不会晕血,后来便不再问了。我听见第一声啼哭、亲手剪了脐带;40岁的时候(去年),有一天他指着幼儿园课本里的天安门说想去看看天安门,第二天,去北京的高铁上,他在我的怀里睡得很香。
然而自己不幸正值壮年却病倒了,幸运的是遇到一位好妻子。那年情人节突然腿疼整晚以致无法行走,下午她陪我去医院。我躺在活动担架上,她推着我一个科室、一个楼层地走。她纤弱的胳膊常常推不直,左扭右拐。我躺着看着她的衣襟,似乎是她在抱着我走。我想到杰克·伦敦的一篇小说《女人的刚毅》:阿拉斯加天寒地冻,淘金的人们都在绝望地逃离,一对夫妇夜晚时发现一个陌生人在帐篷外的火堆旁取暖,女人出去看了一眼回来说那人快要饿死了。天亮后他们看到那人就死在帐篷外。他俩继续赶路,几天后女人也不行了,她告诉丈夫,她知道要走出阿拉斯加,粮食只够一个人吃,于是省下了自己的那一份。男人痛不欲生,女人说,“你一定要活下去,不仅为了我,还为了我的亲哥哥”——那天死在帐篷外的人就是她的亲哥哥,他小时候曾从熊嘴里救出自己,为此被熊咬掉了几根手指,他那晚在帐篷外烤火时她就通过几根断手指认出了他,但却无奈地没有相认……
我确诊癌症一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伏在她身上,抚摸着她柔软温暖的身体,庆幸自己确实还活着。我望着她,她读懂了我的眼神,我把脸埋进她的长发,眼睛湿润了。我体会着她的体温,我真的还活着。
[责任编辑:杨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