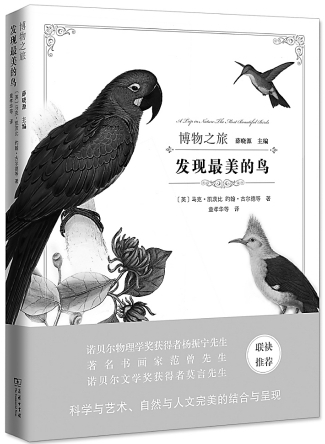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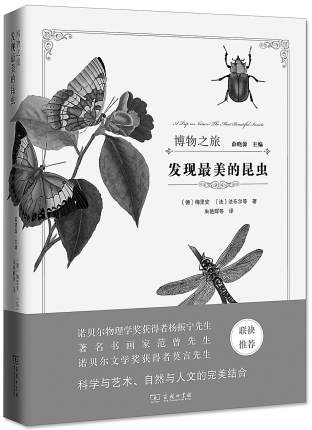
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人类认知的苏醒有两种方式,一是科学认知方式的苏醒,二是哲学认知方式的苏醒。我认为还存在一个美学认知的“苏醒”:一个人从15岁到30岁(大致上),对所在的世界和物质有强烈的求知欲,所学的知识和所解释的范式都标画为明显的科学特征,这一阶段认知我称之为科学的苏醒;从30 岁到 50岁,人的感觉日渐丰富而细腻,学会了认知、感受和欣赏美的事物,人的体力、智力和丰富的阅历呈现感性的风格,对活生生的东西充满非凡的感受力,人的认知方式标画为丰富的感性特征,我们称之为美学的苏醒;50岁之后,人们开始对历史和社会背后的原因感兴趣,并尝试进行解释和阐说,认知方式标画为寻根究底的智性特征,我称之为哲学的苏醒。
西方博物绘画源远流长,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前16世纪希腊圣托里尼岛上一间房屋上的湿壁画,现存于雅典国家博物馆,画面上百合花和燕子交相飞舞。最早的印刷花卉插图于1481年在罗马出版。1530年奥托·布朗菲尔斯的《本草图谱》出版,是一本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为一体的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植物图谱,从此以后博物图谱风靡欧洲。科学家、探险家、画家纷纷加入其行列,涉及人员之多,涉猎范围之广,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在我见过的近百万张博物绘画中,以作者计,在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就有近万人,赫赫有名的有近千人,有大师风范的有近百人。可以概括地说,西方博物绘画发端于十五六世纪,发展于十七八世纪,19世纪呈现发展高峰,作品爆发、大师林立、流派纷呈,19世纪末出现式微,20 世纪出现大幅度衰落,20 世纪下半叶到现在又开始恢复和复兴。
通过近十年的博物学学习和研究,我认为博物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博物绘画对人的科学的苏醒和美学的苏醒大有裨益,因为博物学以及博物绘画呈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一个已经绝迹和正在绝迹的世界、一个色彩斑斓的诗意世界、一个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
一些中国画家认为,西方的博物绘画(他们鄙夷地称之为科学绘画)只具有科学认知价值,很少或者说没有审美价值;他们认为这些博物画画得太死,逼真有余而生动不足。其实他们对西方博物绘画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许多伟大的博物画家像奥杜邦、古尔德、胡克、威尔逊、沃尔夫,都有过人的本领,他们的绘画不光有逼真的线条,而且有斑斓的色彩、丰富的场景和生机勃勃的气势,让人叹为观止!他们艰难跋涉,身入险境,久与鸟兽为伍实地考察是他们成功的保障,很多博物学画家客死异乡他国。优秀的博物画家让铅笔的素描线条、铜板和钢板的制版线条突破了窠臼和限度,表现极有张力,立体地展现了一个多维空间。他们把写实发挥到极致,并用斑斓的色彩和亮丽的光线弥补写实的硬度和呆板,使画面熠熠生辉,充溢着生气,让人有身临其境的美妙感觉。
博物绘画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千面一孔、万象一致的冰冷的印刷复制品泛滥的机械复制时代,在数码相机一统江湖的时代,这些人工手绘的栩栩如生的博物绘画也许在这个日益单向度的世界里,如安徒生童话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夜空的每一支火柴那样,在漆黑冰冷的深夜里带来一小片亮光和些许的温暖。
薛晓源(本文节选自“博物之旅”丛书序言,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