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莎士比亚作品究竟是否出自莎翁之笔一直众说纷纭。近日,林菲尔德大学的丹尼尔·波拉克·佩尔泽教授在《纽约客》撰文,题为“新版牛津《莎士比亚全集》的激进观点(The radical argument of The New Oxford Shakespeare)”,介绍了莎翁考证的最新进展。
去年,盖瑞·泰勒担任主编的新版牛津《莎士比亚全集》出版,这套全集还破天荒地将多位剧作家确认为15部莎士比亚戏剧的合著者,其中包括确认了著名剧作家马洛为《亨利六世》的合著者。在《纽约客》的文中,佩尔泽援引泰勒的话指出,神化莎士比亚造成了世人对其他文艺复兴时期才华相当的剧作家的盲视,而且莎士比亚的历史观、讲故事的方式被确认为典范,而其他的历史想象、讲故事的方式则被忽略。下文为《纽约客》刊登的文章之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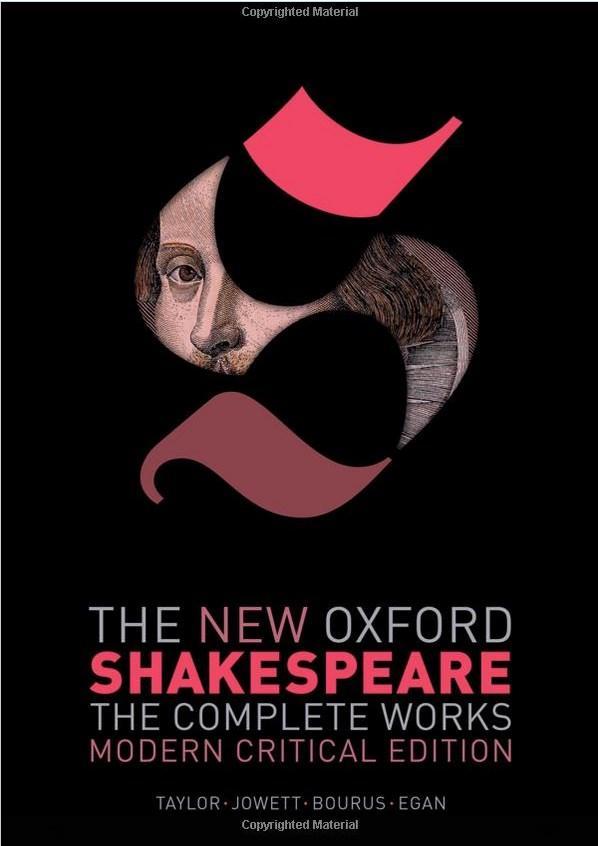
盖瑞·泰勒担任主编的新版牛津《莎士比亚全集》
1989年,一位叫盖瑞·泰勒的年轻学者出了一本书叫《重新发明莎士比亚》,书中认为莎士比亚至高无上的文学地位更多来自那些将他推上神坛的文化制度,而不是他作品本身的伟大。归功于这些文化制度,莎士比亚傲视于文艺复兴时期与他有着同等才华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但他从来不是我们的星系里唯一一颗。”泰勒写道。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抛出这类挑战正统的言论。几年前,他就担任过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的主编之一,这套全集认为莎士比亚的五部戏剧是与人合著的。
去年底,泰勒再一次震惊世人,由他担任第一主编的新版牛津《莎士比亚全集》出版。这套全集第一次把克里斯托弗·马洛认定为《亨利六世》的合著者,主要创作了前三部分。此外,这套全集还列出了其余14部莎士比亚戏剧的合著者——托马斯·纳什、乔治·皮尔、托马斯·海伍德、本·约翰逊、乔治·威尔金斯、托马斯·米德尔顿和约翰·弗莱彻。泰勒是如何发现这些剧作是合著而非莎氏独撰的证据的?答案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早期剧作的语言模式。为此泰勒在一次发布会上打趣说:“现在莎士比亚也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当然,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非他独创产物的观点也早已不新鲜,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16世纪进行戏剧创作有点像今天的剧本创作,往往经多人之手修改后方能付梓。新版牛津莎翁全集认为它的算法可以辨别出哪些作品是以一人之力完成的。但这部新版全集的意义还不在于指出哪些莎翁作品是合力为之,也不在于重新发现并承认与莎翁同等重要却被忽视的剧作家,而是指出,对于莎士比亚的神化决定了他讲故事的方式——尤其是他那种君主中心的历史观——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了毋庸置疑的规范,而实际上存在着其它讲故事的方式,其它的历史观,在这些方面,别的剧作家要比莎士比亚更优秀。

马洛画像
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把马洛和莎士比亚看成一对惺惺相惜的竞争对手。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可能模仿了马洛的《帖木儿》和《浮士德》,《威尼斯商人》可能借鉴了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而马洛在创作自己的悲剧《爱德华二世》时参考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但新版牛津全集所认为的马洛和莎士比亚共同创作了《亨利六世》的观点却并未受到主流认同,而且其数据分析的方法论也广受质疑。
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对莎士比亚的风格进行量化分析。1901年,一位气象学家就雇了两位女性计算莎士比亚及其他著名作家作品中每个词的字母数量。当代的考证学方法则更复杂,但也只是程度有别,而非质的差别。泰勒也曾根据功能词之类的语言学特征来考证,比如像by、so、from这些词很可能是下意识的,很难故意模仿。
对于考证出马洛是《亨利六世》的合著者,泰勒提到最新一期《莎士比亚季刊》的文章。这篇文章检查了一个剧作家如何可能在某个功能词后用另一个功能词。譬如,《哈姆雷特》里那句“With mirth in funeral and with dirge in marriage”里,决定性的词是“and with”,这个功能词的组合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更常见。而马洛式的表达在《亨利六世》中出现多次。该文作文承认他们的方法并不完美,而且可能张冠李戴。
有人指责泰勒说他对莎士比亚怀有恨意,但事实上他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但他认为我们对于莎士比亚的才华的神化造成了我们对于其他卓越剧作家的盲视,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另类政治想象。
“莎士比亚最喜欢的主题是君主制、专偶制、一神制,与此相应的,他最富盛名的台词和十四行诗都是独白。”莎士比亚对唯一性、独一性情有独钟,而泰勒则相信读者的民主,他们喜欢什么东西无需他人置喙。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会借莎士比亚的独一无二来贬低其他剧作家。当批评者发现莎氏早期和晚期作品中某个糟糕的段落或有违和感的地方时,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之怪罪于一个劣等的合著者。莎翁之神圣不可侵犯还体现在,有人会认为其他人的华彩段落其实出自莎翁之手。譬如,佚名之作《托马斯·莫尔爵士》就被认为是莎翁之作,因为笔迹与莎翁现存的六种签名相符。尽管这个理由有点牵强,但想发现新的莎翁手稿的渴望却非常具有诱惑力,他们还硬生生地把莎士比亚和莫尔驳斥反移民暴徒的渗透自由主义色彩的段落联系在一起。是不是只要是莎士比亚,就是好的?或者说只要是好作品,我们就觉得那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出于这种假设,许多编辑往往就会认为《亨利六世》中某些段落出自托马斯·纳什或乔治·皮埃尔之手,这些段落被认为是粗鄙错漏的。马洛全集的编者之一拉斯马森对泰勒把作者考证和艺术价值的判断分开的做法表示赞赏,“如果他吹捧《我该死吗》,每个人都会说,这个戏很垃圾。但如果是莎士比亚,那大家就会说莎士比亚应该是好的,而这部有美学缺陷。大错特错!你随便找一部剧,你都可以发现那些我们认为是莎士比亚的美学上糟糕的地方。”

莎士比亚画像
对于泰勒来说,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看成许多明星中的一颗而非唯一,那将让我们看到其它类型的文学价值,而不是认为如果与莎士比亚不同,那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剧作家就不好。十年来,泰勒坚持认为米德尔顿是“我们另一位莎士比亚”。而就最近报章连篇累牍的报道来看,马洛则有望成为一颗更性感的明星。而且更重要的是,马洛对于《亨利六世》的贡献可能表明存在另一种讲述历史的方式。
在新版牛津《莎士比亚全集》里,《亨利六世》第二部的一个最初的标题是《约克和兰开斯特家族之争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之所以变成《亨利六世》第二部是因为莎士比亚几年前改写了前传。莎士比亚决定把他的历史剧当成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要把君主放在标题里,后来的剧作也是这么印刷的。“如果你把《亨利六世》第二部看成与人合著的,你会看到一种不同的历史剧是如何可能的。”泰勒说。
泰勒的团队将这种不同的历史剧的可能性归功于马洛,相较于莎士比亚侧重男性君主,马洛更侧重于强悍的女性角色如圣女贞德和反叛的平民。
“莎士比亚并没有发明历史剧,他是重新发明了历史剧,使它更强调君主、伟人。如果你意识到《亨利六世》尤其是第二部里有两种政治想象的话,那就非常有意思了。”泰勒说。
泰勒认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想象具有超出文本外的意义。“剧中不止发生着一场政治内战,而且发生着一场美学内战。《争论的第一部分》(The First Part of the Contention)是第一部伟大的英国历史剧。马洛和莎士比亚都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二人都是匠人儿子,都不是在大都市长大的,也都雄心勃勃。这两位非常优秀但迥异的剧作家都在想象新的戏剧形式是什么样的,”泰勒补充道,“可以说莎士比亚赢了,因为马洛被刺杀了。在职业生涯之初,你绝对无法明确判断说莎士比亚更伟大。如果马洛再多活二十年,我们可以想象他会提供非常不同的讲述历史、悲剧和喜剧的模式。”( 文/丹尼尔·波拉克·佩尔泽,编译/沈河西)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