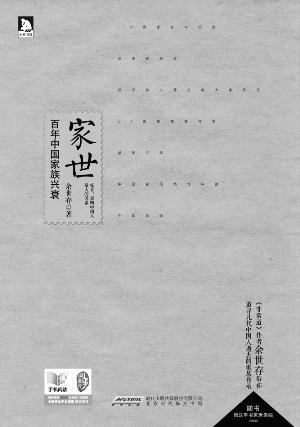
《家世》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学者余世存继《非常道》《大民小国》之后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又一力作。
现代化的危机、社会转型的艰难促使不少有良知的知识人寻找答案,当代人受到空前的教育、信息文明的洗礼,但当代人的“失教”、“粗鄙”、“飘零”、“失去家园故土”等现象有目共睹。余世存的《家世》以记录百年中国家族兴衰,细述名门家事,点评伟人功过,对20世纪以来中国精英人物的家国命运作了一次深情回顾。
记者:您创作《家世》的初衷是什么?
余世存:尽管当代的家庭已经从传统的“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问题仍一以贯之。家世甚至从宗族家庭问题,演变成空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当一家内刊杂志的主编约我写专栏时,我想也没想,就说写家世。我开始梳理百年来的中国家族,挑选我认为值得传述的写成文章。我曾经希望自己能像伟大的司马迁那样纪传前贤,把当代的风范写出来,从而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
有人觉得家世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有点远,觉得普通老百姓就是一辈一辈这样过日子的,不像人家这种大家才有传承,其实不然,《家世》只是讲了这14个家族的故事,实际上《家世》需要的是每一个家庭甚至是每一个人的反思,不只是说我的父辈有什么能传承给我的,包括我自己也可以有值得整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家世》写了宋耀如、黄兴、蒋介石、卢作孚、金庸等大众所熟知的名人家族往事,也写了蔡文彬、杨志鹏等人的普通家族的事迹。您选取的名人家族是出于什么标准?普通家族是怎么选出来的?
余世存:选取名人家族和普通家族的标准并不一致。因为这部书稿断断续续写了多年,言路、思路也不一致。有的选得很刻意,比如林同济家族、蒋介石家族,无论是林家的专业精神,还是蒋家的传统与现代的很好融合,在我看来,都是我们国民极为稀缺的品质。有的家族则选得很随意,这一类标准是,我多少熟悉他们的某个家族成员。比如金庸(查良镛)的查家,我年轻时即认定穆旦(查良铮)是可敬的兄长,穆旦的诗曾经滚瓜烂熟,而金庸也曾应朋友之请送过我签名本画册;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老师是我很熟悉的;宋耀如家、黄兴家,也都是跟其家族的成员打过交道。
至于写了中国人这几年熟悉的老外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书中也写了部分原因。我觉得家风家教以金钱为本位非常需要引人思考,何况经济世袭主义也有人质疑。在技术文明的推动下,“慈善经济”、“散财生活”等新文明的人生价值正在得到广泛地传播,这也是我写老罗家的原因。
普通家族,也是我很熟悉的。我今年曾给年轻朋友开过一个短期课程,课程是“自我整理”,我发现普通人一旦把自己的家族成员、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一个梳理,本身即是一种提升,是对自己生活的加持。故我希望通过介绍普通家族,能够引起读者对自家探索、回顾的兴趣。从目前的反应看,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记者:请您谈谈如何收集到这些家族的故事过程,与这些家族有哪些交往的故事?
余世存:收集家族故事其实途径是多样的,除了公开发表的材料,就是我自己接触,以及朋友交往的。比如梁漱溟先生,我的朋友王康、胡少安先生都曾跟他有过接触,汪丁丁则说梁先生的目光如电,能使来访者心魂为之一动,这些故事让我试图去理解梁先生的人格。
跟卢作孚先生的后人卢晓蓉老师交往给人的印象极深,她是我的北大老师严家炎先生的夫人。她待人接物非常宜人,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特别感动。我跟诗人穆旦家人的交往也值得一说。我曾到南开大学穆旦夫人周与良家,听周先生讲穆旦的往事。从那以后,跟周先生、九叶集之一叶杜运燮先生有过多次交流。
记者:本书中,您个人最欣赏的女性和男性分别是谁,为什么?
余世存:可欣赏的人很多。谈不上最欣赏,但说到女性,宋美龄估计要排第一位。我们当代人对婚姻爱情多半失望甚至绝望,宋美龄遇到的挑战绝对比我们更大。在乱世中,在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个性差异大的情况下,宋美龄加持了她的丈夫,成全了自己和对方,虽有过曲折,他们仍走向了圆满,甚至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不幸福的中国夫妻中,他们的婚姻堪称幸福、完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女人。欣赏的男性有不少,比如卢作孚、梁漱溟、宋耀如等人,都很不错。卢作孚、梁漱溟等是跟毛泽东同龄的伟人或圣贤,他们的力行精神、不惧孤独的勇气,都是我所喜欢的。
内容简介
《家世》以历史散文的笔法,重新解读了近代一些显赫大家族的历史、近事,同时又能深入发掘民间平凡家族的草根史,“平实地写出那些值得‘风范’的人家,发‘修齐’之光”。
作者试图用一种理性而不失温情的笔触,深入地发掘中国现当代著名家族的渊源以及社会变迁大背景下普通家庭的实况,试图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以使人的身心庶几得到慰安”。
作者选择纪传的家族多有代表性,家风家教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或立足专业,或读书第一,或懂得规矩……作者甚至将外人纳入关注、思考范围,如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介绍,提及革命导师马克思、革命诗人海涅、现代哲人罗素、以及当代金融专家们等对罗氏现象的评论,极为精彩。
[责任编辑:杨永青]
